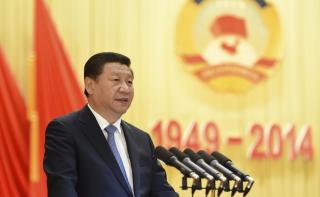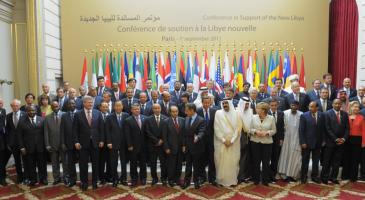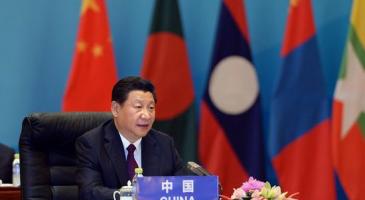我们不需要“注解式赞歌”
【中国经营报】你一直致力于中国改革史的研究,分析晚清大改革的《国运1909》在本报以专栏的形式首发后,受到包括中央高层在内的各方关注。这一次,是什么动机,促使你转入到现实的“一带一路”问题的研究中去?
【雪珥】其实一直以来,我的研究围绕着两个方面:一是你刚才提到的改革史,二是战略史,后者的重点在海洋战略和西进战略。这两个重点,正好与“一带一路”相吻合。
海洋战略史方面,毕竟我身处澳大利亚,与东南亚相邻,那里本是历史上华人移民拓殖的重点区域,便于观察中国海洋战略历史发展。近几年,我每年冬季也会在海南呆上一段时间,近距离地与身处第一线的渔民等有所接触,尤其在最为深入南沙海域的潭门镇,得到不少启发(参阅雪珥文章《放牧南沙:一条经略南海的商界思路》,本报2013年3月16日)我也担任了“海南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”的研究员,得以结识一群优秀的一线学者。
西进战略史方面,这几年我花了不少精力,研究清代以来中国的新疆、西藏政策以及与中亚、南亚次大陆的关系史,侧重于历史对当下的政策借鉴意义。仅2013、2014年,我就8次入疆,其中深入南疆地区3次,还担任了南疆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“塔里木大学”的特聘教授。无论是南海课题、还是新疆课题,因为着眼于政策研究、实务研究,而非学术研究,实际上融合了“改革史”与“战略史”。
中国官方提出“一带一路”并大力推动之后,媒体与学界都很热闹,但我感觉,大多数还是唱赞歌为主,只是学界的赞歌比媒体的更多了点技术含量,算是“注解式的赞歌”。大多数笔墨都在论证愿景的美好与伟大,却似乎不很关注如何连接丰满的理想与骨干的现实。那些侧重于技术操盘层面上的研究,似乎尚未被主流舆论所关注。一些体制内的研究机构,把 “一带一路”当作争取、或者争夺经费的一个新工具,“瓶子”与时俱进了,“酒”却依然如旧,这大约也是中国学界的老常态。
《中国经营报》:不只是学界,政府和企业似乎也没有做好相应准备。
雪珥:对。地方政府对于“一带一路”的响应很热闹,一些还推出了经由新疆联通欧洲的所谓“x新欧铁路”,甚至花了大量公帑造势以争夺丝路起点的称号。遗憾的是,还可算是实务层面的各条“x新欧铁路”,地方政府只是大赞其美好愿景,很少提及实际经营成本与效益,以及中长期经营思路。而据我所知,这些“x新欧铁路”至今几乎没有盈利的,都在赔本赚吆喝。更深一层的是,这种吆喝究竟是给谁听呢?显然不是市场,而是领导。我不客气地说,这依然是官僚主义的惯性,用一种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学舌以及成本高昂的做秀,猎取“紧跟”的官场红利,这既不利于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,更不符合实干兴邦的要义。而在各条“x新欧铁路”上,目前真正要考虑的,可能并非建路(路早已有了,无非需要在硬件和软件、如通关上升级),而是拿什么货物去填充这条成本并不低廉的路。
至于企业界,目前在“一带一路”上活跃的,主要还是国有企业,民营企业的比例并不高。正如我文章里所说,“国企习惯不负责、民企习惯钻空子”,这些不仅带来了问题、损失,也可能导致一个好的战略在执行环节上走样、变形、异化。
战略确定之后,关键在于细化、落实和执行,绝不仅仅是宣传、尤其不是唱赞歌的宣传。我曾经长期做企业,坚信那些无法执行、无法落地,或者不去执行、不去落地的方案,就是空谈。我也习惯了做SWOT分析(优势Strength、劣势Weakness、机会Opportunity、威胁Threats),并尤重其中的W(劣势Weakness)和T(威胁Threats)及其应对之道。作为一名研究者,我因此从“一带一路”的风险应对入手,并通过媒体与政商两界的“需求者”互动。
《中国经营报》:也就是说,正是这些“唱赞歌式的宣传”,促使你把研究的目光转向这一领域的薄弱点?
雪珥:坦白说,《中国企业如何安全走上一带一路》一文其实还是很粗糙的一个研究心得,囿于经费及时间的限制,我并没有将更多、更新的海外研究数据用上。该文在《中国经营报》发表后,受到的广泛关注大大超出我的预料。作为一位“非职业”的研究者,我很清醒,这些关注与其说是对我文章的赞赏,不如说是对我视角的认同。我所希望的,就是以此“抛砖引玉”,希望更多的“职业”研究者们能看到“市场”对实务研究有多么巨大的、甚至饥渴的需求,将自己的才智少放些到“注解式的赞歌”里,多投入到实务研究上;并且,用好媒体的渠道,与“市场”上需求者们保持密切的互动,让研究真正服务于实践。
一带一路是百年战略
【中国经营报】你在研究中接触到很多实际案例,对你触动最大的是什么?
【雪珥】有一年,我的一些企业家朋友,准备了好几十亿到南亚某国投资,但是,他们对那边的情况实际不托底,心里发虚,费劲去请了些退休的外交官咨询。大多数中国企业,甚至包括国有企业在内,其实对“走出去”的目的地缺乏基本的了解,更遑论细致的、深刻的认知。而现有的体制机制下,能为企业提供的更有针对性的信息指引并不多,广义上的“情报”服务,效率并不高。
在我接触到的实际案例中,首先就是这类有实力走出去、也有意愿走出去的企业,其对信息的需求,很难得到有效的满足。这需要外交机构、其它政府部门及学界、媒体共同努力。
其次就是中国企业在外面吃了很多亏。有的亏是“战略性”的,比如中国企业的并购因政治原因遭遇搁浅,这种亏,国企吃的多。有的亏,则实在没有技术含量,比如因为轻信对方、甚至合同都没有好好签、“市调”(市场调研)也没有好好做,这种亏,民营企业吃的更多些。走出去的民营企业,一些固然是企业做大做强之后的“外溢”,还有些则是纯粹想到国外去捞第一桶金的,各方面的实力、能力、资历都不具备,把中亚、南亚当作80年代的中国,以为凭着胆大就能掘金,却不知那毕竟不是你的主场,盲目走出去,最后无谓地耗用经济乃至政治、外交资源。
第三,一些中国企业在高腐败、高风险的国家,不仅生存了下来,甚至还颇有如鱼得水的感觉。比如我的一些温州老乡,在某些小国投资,真可谓是风云人物,可以随时见总统、总理,甚至其企业还拥有兵力不小的保安部队。这些令我思考:务实地看,东道国的高腐败、高风险,不能一概当作不利因素,也许在某种程度上、某个时段内,没准还是中国企业特殊的“竞争优势”所在呢。
【中国经营报】从国家发展战略来考虑,你认为一带一路的最大意义是什么?
【雪珥】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,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体系的主要成员,体量大、分量重、影响力强。到了这种体量,利益格局、利益诉求自然不同于当年,利益线也远远比当年更为广大,很自然就必须考虑:一、如何维持进一步发展;二、如何保护既得利益及新增利益。
从历史上看,凡大国崛起,随着体量的增大,都有一个明确的、长期的全球战略,以适应新的体量、获取新的增长空间。特别值得关切的,是美国的太平洋战略,从1850年代成型,到1870年代内战结束开始全面推行,直到1940年代,一以贯之,实现了其“太平洋帝国”的梦想,余音持续至今。
近一两百年来,中国一直被动地应对西方的刺激,中国近现代史也成为典型的“刺激-反应”型,“救亡”成为最大的、最紧迫的任务,难以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。经历了一百多年的“救亡”,尤其是近三十多年的经济腾飞,中国终于有财力、物力来从容考虑更为长远的战略,这无疑是中华民族的幸事。
我个人认为,“一带一路”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第一个真正的、可能主导今后一两个世纪的国家战略。尤其是陆上的“一带”,通过打通欧亚大陆桥,减缓对南海航道的过度依赖,变向南的“单腿走”为向南、向西的“双腿走”,构建中华的“双头鹰”,其意义丝毫不亚于美国在1850年代制定的所谓“太平洋战略”。如何一步步落实,则是对今后几代、甚至十几代中国人勇气、智慧和耐性的考验。
值得注意的是,国内有一种论调,认为少用“战略”、“西进”、“桥头堡”等词汇,担心被人家当作“中国威胁论”。这种顾虑,把国内舆论都定位成了外交部发言人,总是担心友邦惊诧,同时也小看了国际社会:战略博弈岂在几个词汇上,换了几个词,人家就不再疑虑了?这种“自疑”,其实依然是不够自信的表现,总想看人家脸色。美国搞TPP(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),就从来不讳言其战略意义,其新任国防部长阿什顿﹒卡特甚至公开宣扬,就广义的再平衡战略而言,TPP与一艘航母一样重要。
【中国经营报】你之前一直研究新疆问题,也多次深入新疆地区做实地考察,你认为一带一路的推进对新疆的维稳和发展是否也有现实意义?
【雪珥】新疆作为“一带一路”核心区,既是最大的受益区,也是最为重要的发力区。
历史上,新疆的维稳与发展,曾受益于类似的定位布局。乾隆时,中国收复新疆,就在南疆地区大力推行货币改革、政府职能简化、法制建设、吸引外来投资、鼓励内贸外贸等,令南疆地区迅速实现繁荣,当时的英国学者包罗杰(Demetrius Charles Boulger)受英国政府委派,对南疆进行考察,对此倍加赞赏,认为中国“很快就使之(南疆)成为中亚最繁荣幸福的地区。”可以说,这是乾隆版的“一带”。
不仅如此,彼时的中央政府,也大力推动新疆与东部沿海的经济往来,“把该地区和西藏引入国际贸易范围”(美国汉学家穆素洁Sucheta Mazumdar),“江南的商人能够贩卖丝绸到新疆获利。”(美国汉学家濮德培Peter Perdue)这实际上是将其与东部沿海丰沛的海外经济渠道接轨,将新疆纳入了“海上丝路”,这可谓是乾隆版的“一路”。
当然,乾隆版的“一带一路”,还称不上战略,其广度、深度、力度,与今日的“一带一路”不可比拟。即便如此,乾隆版的“一带一路”也为新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大变局中,新疆依然牢牢地置身于中国的怀抱而金瓯无缺,追根溯源,还是要归功于乾隆时期开始的政策对路。
有关新疆与“一带一路”的关系,无论在新疆还是内地,我感觉最大的问题或许依然在于:对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的伟大、必要及其对新疆的重要性,着墨过多,相对在实务上下功夫的少;讨论总是围绕着why(为什么),而比较少地深入到how(如何办);谈论新疆的S(Strength,优势)与O(Opportunity,机会)多,W(Weakness,劣势)与T(Threats,威胁)少……我觉得,这不仅是文风,也是作风,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。
务实不务虚、实干不空谈,以问题倒逼改革,以工匠精神推动建设,这大约是“一带一路”最需要、也是最紧缺的。
我们必须面对高风险
【中国经营报】我们回到商业层面,你在前文中虽然深入研究的是一带一路地区的投资风险,但前提却是中国企业必须走进一带一路,抛却国家战略和政治考量,你认为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带来的机遇在哪里?
【雪珥】其实,对于相当多一些企业,国家层面的战略与政治考量本身,对企业的利益也是息息相关的。
我曾与西部某地一位政府主官畅谈,他们在努力吸引东部的一家外向型家电制造大型企业,最初的考量仅仅是要填充“x新欧铁路”的运能,减少“x新欧铁路”的亏损。走这条铁路到欧洲市场,比海路大约节省至少1/3的行程,对那家企业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。但是,“x新欧铁路”因为整体运能依然大量闲置,导致单位运输成本无法有效降低,算下来,投入产出比还是有一个缺口,企业就很犹豫,地方政府也在犹豫是否要通过减免地方税收去填补。其实,地方政府还是准备下决心的,因为只要这家大企业入住,“x新欧铁路”的运能利用率会大大提高,进而拉低单位运输成本,对后续企业就有极大的吸引力。但企业需要考虑的是:要充分享受“x新欧铁路”的好处,就必须考虑将制造基地全部转移到西部,否则,从东部沿海的生产基地到西部的“x新欧铁路”起点,还有一笔不菲的本土运输成本。实际上,这就牵涉到了另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:东西部的产业转移。
“一带”战略令西部地区从“臀位”变成了中国“双头鹰”的另一个“头位”,西部、尤其是那些既能连接欧亚铁路,又能通过长江航道连接东部的城市,如重庆、武汉等,其区位优势明显加强,如能外接“一带”,内接转移出来的东部产业,则“一带一路”大战略能够策应、或者说倒逼国内改革。这其中所蕴含的巨大商机,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存在。值得欣慰的是,西部地区的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思考具体的操作。
至于“一带一路”给具体产业带来的利好,基建、交通类无疑是最先受益者,这在股市上也颇有体现。但是,我觉得还有一种“基建类”被普遍忽视了——那就是法律、金融乃至小语种翻译服务等专业服务。“一带一路”沿线主要国家,与中国此前的主要贸易伙伴,大多并不重叠,对中国大多数企业来说,是全新的市场,有着许多未知的风险,而法律、金融等提供的恰恰是软性的“基建”。这些“软基建”,与“硬基建”一起,应该是“一带一路”的第一批受益者。
至于内媒、外媒都曾经热炒的“过剩产能转移”,倘或真能实现,当然对备受产能过剩困扰的中国企业来说,是利好消息。但是,产能转移必须关注一个前提:市场是否相应地转移并扩大?“一带一路”上的新市场,能否消化那些转移出去的产能?倘或不能,依然过剩的产能怎么办?如果市场没有相应扩大,“一带一路”对于中国过剩产能转移的意义,可能仅仅局限于获取替代的廉价劳动力上。正是在此意义上,“创新”对于中国经济转型才有更为关键的作用。接下来的悖论是:如果“创新”缺位,“一带一路”又难以迅速提供足够大的新市场,企业走出去的动力何在?而如果注重“创新”且能够“创新”,企业又何必万里迢迢到“制度质量”并不好的“一带一路”新环境里去呢? 从这个角度看,有关部门不希望将“一带一路”过多与“产能转移”挂钩,或许不仅仅是为了外宣形象,而是“产能转移”本身并不十分靠谱。
【中国经营报】你在写此篇文章时,精读了15万字的一手材料,读完之后,你对一带一路地区的直观印象是什么?这个地区是理想的投资区域吗?
【雪珥】我曾经长期经商,所谓“理想的投资区域”,弹性实在太大,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风险偏好,更有不同的竞争优势,这都影响着对“理想”与否的判断。
从大量的材料来看,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,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,不仅经济上如此,政治上也如此。这些国家大多数在法治健全、政府廉洁、社会稳定等方面有很大缺陷,正如我在那篇文章所言,“一带一路”实际上是高腐败带、高风险路。需要强调的是,这并非我的价值判断,而只是客观描述。
接下来的问题就是:即便高腐败、高风险,难道就不是理想的投资区域了吗?显然,单单从中国自身这三十多年吸引外资的经验看,绝非如此。历史上发达国家崛起的轨迹可以表明,虽然高风险未必带来高利润——促成高利润实现还需很多别的因素,这些因素决定了对风险的消化及转化能力——但高利润一定伴随着高风险。并且,作为后发国家,还有个现实问题必须面对:你来迟了,容易下口的肉和汤早已被人家吃了,除了啃骨头或者另觅食物之外还有别的选择吗? 因担忧风险而裹足不前,是最不可取的。
中国企业该发挥适应“浑水”的优势
【中国经营报】你在文章中提到过,中国的政商关系下,养成了“国企习惯不负责,民企习惯钻空子”这一特点,这样的特点在一带一路地区,恐怕有负面的作用,也有正面的作用,您是否能分析一下这两方面的作用?
【雪珥】“国企习惯不负责、民企习惯钻空子”,非要挖掘其正面作用,那可能就是因此养成的对风险的过度迟钝或许倒强化了冒险精神——但这是一种“傻大胆”的冒险精神。
在我的文章中,引用了很多专家的研究,说明了中国企业对风险或许有特殊的承受能力。“一带一路”上的政商环境,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的政商环境比较接近,这意味着中国企业或许能比发达国家的同行更能适应这种环境。
必须看到,在今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,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这种国情,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,你要么适应、要么远离,任何试图进行改造的努力,都必然是无用功、甚至负作用。如果能将中国企业对“浑水”的适应能力,辅以更为精确、全面的风险研究、控制、应对,也算是“物尽其用”的做法。生意就是生意,还是少些理想主义、少些道德原教旨主义为好。
“不负责”这个特点,绝对没有正能量;“钻空子”这个特点则是中性的,毕竟资本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,但必须升级、提升其技术含量。
【中国经营报】你认为,想要安全地投资一带一路地区,国企最应该做什么?民企最应该做什么?
【雪珥】无论国企、民企,对于风险,首先还是那“三不”:
一、【不害怕】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,全球资本史证明了富贵还是要险中求的,何况他人能往、我为何不能往;
二、【不回避】正视风险,不要做鸵鸟,少唱空洞的赞歌,多研究实际问题;
三、【不轻视】战术上高度重视,不断探索切实的解决之道。
国企“走出去”所承担的风险有两大类,一是因国家战略需要(比如解决能源供给)而承受的风险,二是因企业内部管理失控而造成的风险。前者是战略风险,但必须防范管理风险加剧、放大战略风险;而后者作为管理风险,自然倒逼到国企改革的老问题上了。因此,我总是认为,归根到底,所谓的风险主要在内、而不在外。
至于民企的“走出去”,很多是经验型的,在“吃一堑”之前很难“长一智”,包括政府在内的旁人再操心也白搭,这大约也是转型期的难以回避的成本。当然,加强风险的研究及应对措施的研发,比如建立健全投资担保体系等,最终能帮助民企少“吃”几“堑”,或者至少在其“吃一堑”后能提供“长一智”的有效工具。
【中国经营报】一带一路是国家战略,说到底,国家应该为企业进入一带一路地区保驾护航。就您的研究来看,国家目前为企业进入一带一路,最迫切的工作都有哪些?
【雪珥】如同政府在国内为企业发展应该做的一样,重点还是是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,当然具体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类型有所区别。比如,外交机构应该加大针对性的信息服务、风险研究、危机应对预案、法律及政治后援;对根据双边条约、需要特别准入的行业,加强当事企业事先的风险防范等……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很多国家,并非“法治”(Rule of law),充其量只是“法制”(rule by law),甚至只是人治,更有针对性的双边外交条约能有效弥补这些制度缺陷。
其次是产业投资引导,鉴于“一带一路”并非单纯的经济开发,动辄需要耗用国家的外交资源等,对“走出去”的产业、企业应当通过信贷等杠杆进行调控,减少那些在资金、技术、管理上非常落后的企业对外盲目投资。
第三就是金融扶持,除了类似“亚投行”这样的银行机构外,是否还需要投资保险机构这样的集扶持与约束功能于一体的工具。
【中国经营报】最后我们再回到战略层面,您也是一位历史学者,您认为中国以往的西北政策、对中亚的政策以及中俄政策,对于今天发展一带一路战略,有哪些借鉴意义?
【雪珥】中国历史上的“筹边”,有不少经验、更有不少教训,而核心问题在于:那些“筹边”往往是短期行为,常常受制于短期的国内政治需要而旋起旋灭,缺乏国家层面上的长久战略。
“一带一路”既然确定了,首先就要坚韧地予以推进,不能轻言放弃。史上强国的全球战略,无一不是“熬”出来的,面对各种困难,及时调整,但绝不放弃。何况,中国如今发展到了一个瓶颈,没有任何余地可以轻言放弃的,逆水行舟,不进则退。